刘燕华 仇保兴:国家中心城市实施创新驱动和品牌战略的若干建议
点击数:3057 字号:小 中 大
依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全球城市的提出者沙森(Sassen)的说法:在经济社会全球化时代,国家级中心城市主要的功能是争夺全球高等资源而不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初级资本。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造业的比重下滑并不可怕,令人担忧的是决定制造业命运前途的科技创新的衰落和社会投机习俗的持续强化。
所以,对我国中心城市来说,未来的发展成也是“旧制造业”,败也是“旧制造业”,思路被锁定了,难免在“旧制造业”中绕来绕去。解决之道是实施技术创新战略、重振当地制造品牌,建议关注以下七个工作重点。
一、知识经济时期,促进技术创新应有新思路
现在是“新经济”的时代,也称“知识经济”时代,其有三个特点:新知识的涌现、新价值的创造、新业态的扩散。
第一,沉默知识共振欠缺。新经济的发展与新知识涌现密切相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把知识分为两个体系,一个叫显性知识,一个叫隐性知识(又称沉默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专利、论文等形式发表,可以出版或在网络上传播;但是沉默知识往往难以形成文字,只能“意会”,这类知识占到了知识体系的90%,只有沉默知识的碰撞才会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技术。但是,中心城市科技管理者不大注意沉默知识的培育与碰撞,只注意显性知识,忽视沉默等于延缓了科技创新。比如说过分重论文、重文凭实际上就是只重显性知识的表现之一。
第二,对“草根人才”尊重不够。新技术变化极快,例如纳米、基因蛋白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大学相应的专业都尚未形成。这些领域的知识往往并不掌握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手中,不掌握在老院士手里,而是掌握在二十年前的马云、马化腾、任正非这样的草根人才手里(老牌中心城市往往很现实,看重的是职称、资金、专利。)。这些老牌城市对草根人才其实是不够尊重的,尊重的是有名气、有地位的(干部和企业也都注重讲级别和名头)。
第三,高度包容创业自由度不够。新知识涌现要高度包容,要有创业自由度。1999年初,我任杭州市市长时,曾提出“密集型人力资本发展战略”,城市的未来实际上决定于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该战略提出优先考虑密集的人力资本的占有和活力,提出了“游在杭州、住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战略举措,这四个“在”就是围绕知识和人才所提的。因此,近十多年来杭州的GDP发展比较快。
许多在老牌大城市有过创业经历的科技人员认为,这些城市“不缺规则,缺包容;不缺服务,缺创新;不缺旧制造,而缺新经济;不缺人才,但缺机制”。“旧经济”会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财富,“新经济”却是新创造的知识财富,是无中生有的。新价值的创造,最需要的是为大批新型企业家自主自由发展创造环境。发展新经济应当“包容”吸引更多创新的企业家,要容忍“适度的混乱”。许多城市科技管理者一讲创新,往往就是投入、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其实硅谷就是美国最“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地方。知识产权是“双刃之剑”,硅谷是对知识产权转移包容度最高的地区。包容还体现在对各种科技创新活动的自由度的扩展等方面。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中曾有座占地2万平米的多层大楼,建于1943年,这座原本计划在二战结束后就拆除的“临时建筑”20号楼,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拆除重建,在此期间产生了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50多位美国科学院的院士,这座临时建筑被誉为“拥有独特的灵魂,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

我国中心城市却鲜有MIT20号楼这样的地方。用地分类和城市规划管理的精细化造成什么东西都是清清晰晰的。北京曾有“乱搭乱建”的办公楼,深圳有“综合社区”和学自香港的“法定图则”(规定了几项负面清单项目之外,建设改建就比较自由),特区外还有许多违法建筑、大量城中村也降低了创业成本。讲规则是好事,但是“20号楼”这种适度混乱的科技创新载体也就消亡了。
二、全球化时代争夺顶尖人才是中心城市的重要使命
新经济需要有“新激励”。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是什么?应是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高端资源的城市,从而示范引领全国产业链升级。现在是争夺全球资源的最好的时机,21世纪什么都贵,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相对便宜。特别是现在美国政府调查华裔人才、排挤大陆留学人才,正是吸引他们回国创业大好时机。同时,俄罗斯、乌克兰等东欧国家长期处于经济滑坡阶段,科研经费骤减,这些国家的人才纷纷找出路,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机会,可以敞开大门争夺人才。中心城市要有超前的战略思想,要面向全球、用最大的力度来找人才、抢人才、用人才。要提出以“空间换技术”,新技术是不确定的,但是有多少建筑空间可供创新者使用是确定的。同时要以“硬环境”来引“软技术”,“硬环境”成本低、质量高,坚持以人为本,人才就会在我国大城市聚集(现在不少城市房价那么高,谁会去创业呢?)
华大基因2000年从北京迁到杭州,市政府就借了它5000万贷款,科技部给的超级计算机,浙江省政府补贴一半,中央政府补贴另一半,华大基因一下子就买了5台超级计算机,很多的成果都是在杭州做出来的。后来华大基因去了深圳,成了深圳的科创领军企业。华大基因声称自己不产生GDP,而生产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和新思路。许多新兴中心城市缺的就是这样的企业,缺的是能够产生知识创新的源头性的科技机构。在知识经济时代,原创性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品”,就是要用钱砸出来的、是优质投资环境育出来的(如果仅认为科技创新是市场机制造就的,是不足的)。
三、协调城市群发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集群
新业态的扩散要求企业应当充分“平台化”,但是老牌大城市的大企业往往还是集中控制为主,还是沿用工业文明时代流行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体制。企业今后应当成为个人创业服务的平台,把个人创新的不确定风险用企业的平台去中和掉。新经济时代是个人创新、创业爆炸性发展的时代,我国老牌中心城市人才很多,但很多跑到外地去“爆炸”了。
“平台集群化”就意味着企业应当是做好微笑曲线两端,把这两端留在大城市,当然也要为周边城市的企业集群植入技术源。例如浙江省有500个企业集群,大都缺乏技术源,跟上海的融合紧密度不够。因而,北京、上海要帮助长三角、京津冀其它城市,真正成为企业集群技术升级的推手和引路人。但许多干部缺乏对企业集群的认知。其实,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波特就曾指出: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并不是由那些大工程、大企业来构成,反而取决于那些在地理空间上不起眼的“马赛克”——企业集群。例如台湾地区的芯片制造为什么具有国际竞争力,因为它是集群化的。比如,美国半导体芯片的博览会一般能开十天,第一天如果有客户提出某种芯片的新要求,展览会还没有结束,台湾将样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芯片的设计、原料、光刻、封装、测试等环节都已经靠台湾的集成电路集群企业分散创新完成,美国人都震惊了,这就是集群的力量(企业集群还可使创新的风险成百倍减少)。美国政府最怕的就是台湾与大陆经济的融合发展。
集群一定要协同,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于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包括“龙尾、龙头、龙身上的每个鳞片”都要有竞争力,在世界上都要能排上名,这样竞争力再聚合才是非常强的,如果能达到这种状态,什么国际贸易摩擦都不在话下。某类商品是否存在由企业集群构成的产业链差别是巨大的,可以影响成本达30%-50%。但是,我国许多产业集群并没有在中心城市的引领下实现协同化发展。比如,丰田把汽车生产扩散到周边,然后全部用工业互联网连接,在物流和柔性生产线上的空间/时间位置精确到零点几秒钟,库存几乎为零,生产成本大为降低。集群对创新活动具有足够的柔性,创新成果可以迅速扩散,集群结构也可以是“去中心式”的,创新的成果可以不断从下而上地涌现。集群作为生产制造系统演化的新形式,创新和扩散能力是受每个主体—企业自适应能力长期影响的,其结果是政府难以预料的。城市在打造新业态时,可以说“成也是区域,败也是区域(现在周边的城市是各走各的路,与中心城市没有多大关系,中心城市有的技术,别的城市也有;结构雷同,互补性差)”,这些问题应靠产业链整合来解决。
四、用工业4.0的思想来打造未来的制造业
德国工业4.0是瞄准了9大前沿技术,在德国打造9大平台集群,这些集群通过智能联络,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企业家和商人在这里运作,平台可以提供服务,包括标准服务、法律服务、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等,通过这种服务,使高端人才向平台集聚,这是一种“后工业化思维方式”。
国内城市传统科技和产业规划仍然是一种旧品牌思想。比如说瞄准十项技术、生产十大产品、培育十大国企,这还是“插小红旗”的做法。以为做点外壳,买点技术,就把品牌做出来了,这是“产品思想”。人家卖给你,你就是品牌,但是人家如果不卖给你,你就不是品牌,所以这还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延续。
技术并购可能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值得赞扬。国家中心城市既然瞄准了新型制造业,就是要用工业4.0的思想来打造未来的制造业,而不是当前的制造业,这个主导方向必须明确。
五、“中国制造”应主动补缺工作母机、仪器、试剂等全国“短板”
中国制造业不缺制造能力和廉价劳动力,最大的短板是缺工作母机、仪器、精密试剂和高端工作设备。国内那么多高新技术企业,大部分整套的设备都是进口的,这是受制于人的。研究院所里面最先进的设备仪器也都是国外的。中国科技经费每年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40%的经费是用来购买国外设备。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制造就可以翻身了。中心城市要瞄准工作母机和关键设备的研发,这些都代表着“标准”和国际竞争力。
六、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要尽快“谋定而动”
与传统制造相比,新兴制造业的运行模式、技术能力、标准、竞争特点都大不一样了,国家中心城市瞄准的到底是什么制造业?传统制造可能很快就没了,不能再把汽柴油车作为制造业品牌来树了。应当是“新型汽车”,而不是“传统汽车”。欧盟已经提出来了,2025年开始不再制造传统汽车,全转型了,正在准备把旧车卖出的时候,我们又准备去买,不是又上当了吗?所以还是要瞄准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可以梳理一下,比如信息技术、能源技术、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要瞄准这些新技术,特别是制造业,更要推行“智能制造”,以后的“黑色工厂”(无人工厂)是普遍的,智能机器人进入到全社会了。将来,中国的制造业不是给别人做“配件”的制造业,而是要引领新的消费的制造业,要能够创造新的消费市场。
七、注重创新软实力的培育是当务之急
打造品牌其实也是鲤鱼跳龙门,但是如果“水离龙门有十丈八丈高,再好的鲤鱼也跳不过去,如果把水位抬高,千万条鲤鱼都能跳过去”。对国家中心城市来说,更重要的是“改良土壤,提高水位,建创新高速路”服务于周边区域的企业群。创新是生产力,但是创新中的生产关系出现了严重缺陷。现在还是用“产生问题的思路来解决问题”,这是不行的,必须用“未来倒逼现在”,引进人才的能力其实就是生产力。
这次机构改革,刘鹤副总理又管科技又管工业,国家成立了新的领导小组,过去叫“科教领导小组”,现在叫“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是一种体系建设和制度安排,说明到了改变生产关系的时候了。制造业也要有生产关系改变的方式,打破“通仓式”的垄断,解决“小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几十亿的大项目最后也是分到小作坊去做;解决“条块分割”,实现“区域共享”。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创新生态环境构建方面应该走在前面,要通过制度改革使中心城市的“新制造”带领产业集群升级、引领全国中心城市经济转型。
深圳南山区吸引的国际性人才非常之多,不是光提供钱、提供房子,而是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对于硅谷来说,硅谷没有出台过任何一项福利政策,却可以在全世界70亿人中挑选精英,它给人才的是预期,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小恩小惠。我们也在进行科技体制创新的调研,发现深圳也在学这个,但许多中心城市却没有学,还是在考虑给人才项目、给点奖励、给点补贴,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些城市必须加快创新软实力建设,争取早日提上日程。任何品牌是要有根基的,以前是游击战,现在是阵地战;以前是单兵作战,现在靠联合作战;以前是靠人力作战,现在靠智慧、靠智能作战。在新时期,科技创新驱动路径已不一样了,城市领导人应当有新的想法,要打造真正能够拉动本地,又能带动全国的制造业品牌。国家级中心城市如果把精细化服务和创造力培育结合起来,将会真正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作者刘燕华系欧亚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副部长;仇保兴系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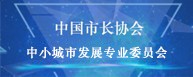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1495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1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