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春: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类型分析与路径选择
点击数:17592 字号:小 中 大
全球价值链体系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源于美英等国的新自由主义,催生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流动性为媒介的全球化浪潮,建构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当世界从旧全球劳动地域分工转向新全球劳动地域分工,意味着各国及其城市在日益联系紧密的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作用被重新定义和塑造。当这个世界步入信息时代和高技术时代,新的全球“中心—边缘”格局表明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和交易中心下(在自由流动和网络化的体系中,控制权或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以及快速发展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的“反向”压迫下,煤炭、石油等资源型产品的重要性和市场价值相对下降。同时,中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从全球产业体系的架构来看,仍处于“半边缘”向“半中心”转型的过程中,即仍处于向全球供给初级产品(甚至包括部分原材料)和初、中级加工的传统工业品的状态,很多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往往是在华的跨国公司生产,其关键技术并不在我国手中。如此,全球化进程伴随着国家发展政策变化,资源型城市的地位、价值、区位、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发展路径随之需要调适。
我国当前在技术、管理层面存在升级换代的“瓶颈”,产业链在全球层面处于中低端,需要深层次的智力支撑和技术体系的创新。如制造业可替代性较高,出口商品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并在近十年调研机构相关调研(Consumer Survey)的国家制造业品牌实力排名和口碑排行榜中名次都偏后。工信部2018年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表明“卡脖子”的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技术水平高的产品严重依赖进口。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需要突破技术、开拓新市场。在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中处于中低端、利润薄、竞争强的传统资源型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一个城市层面的升级换代绝非易事,因为这同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压力和竞争。
当前,国内学术界给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核心策略是:至少应在其资源开发“由盛转衰”这个临界点,或者更早的时间点,着力推进资源型相关新产品的研发和升级,培育接续型产业和新发展要素,采取新产业战略(引入全新替代产业的“大转型”)或产业链延伸战略(延伸产业链的小转型)。杨振超(2010)提出建立循环经济体系来破除“产业锁定”,建立新产业优势和推动产业多元化来促进城市的全面转型。这种转型策略及其路径存在几种限制:一是这个资源型城市需要具备相关的技术进步或吸收新技术的能力或条件。如若不具备技术研发和吸收能力,通常需要省区或国家的大力支持。二是部分资源型城市因为区位限制(如偏僻、闭塞、成本太高等)或条件太差,缺乏在市场条件下吸引高品质发展要素的条件或可能,即使省区或国家的大力支持,也存在不可持续性,因此缺乏继续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如地处边疆和位置偏僻的部分资源型城市。三是资源型城市所涉及的主要高附加值产业链已被其他城市或跨国公司掌握,自身的产业升级缺乏竞争力,无法实现预想的目标。
由此,我们可判定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在一定的成本—收益约束下或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些资源型城市转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二是即使有成功的可能,其关键在于有能力吸纳新技术、人才等资源,能生产出有竞争力适销市场的新产品,并能融入国家或全球的市场体系和产业体系。由此,资源型城市能否成功转型的两大要素是区位优势和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体系(或新产业集群)。在国家或全球层面,这些传统的资源型城市需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总部所在的世界城市或我国的全球城市或专业性全球城市发生联系,连接国家或全球生产网络,成为这个经济网络的重要组成单元,至少成为能融入全球性功能的专业化城市。
空间收缩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类型划分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研究显示,近20年来,我国的人口和中高端产业不断向东中部地区和西部的城市群或中心城市集聚,边缘地区或边疆地区乡村人口总体上处于流失状态。随着就业机会、居民收入和人居环境差距的拉大,这种趋势仍将持续。在这种国家尺度的空间收缩背景下,位于东北、西部和中部丘陵地区的资源型城市不同程度地面临人口等资源流失的问题,尤其是高端人才及其技术资源的流失,这可能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换代。基于城市尺度的产业升级和调整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如吸引投资、引进人才和国家支持,将可能产生“断裂”。因此,部分资源型城市需要和区域内的中心城市结成“发展联盟”,通过建构区域性的产业链或区域产业的整体升级促进城市的转型。有些偏远型或高端资源不足的资源型城市需要调整甚至放弃“囿于一地”这种传统的产业转型策略,通过区域性的产业协作方式,如城市群或网络化的城镇体系,融入全球产业链和日益复杂的城市网络来实现城市转型,探索城市转型的新路径。
可以肯定,我国资源型城市大规模、全面性、地方性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市场化、网络化、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困难,需从“流动性”和“全球性”角度出发,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分为“扩张态”“稳定态”和“收缩态”三大类。实际上,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传统思路整体上仍建立在基于增长预期或扩张惯性的思维定式上,需要彻底反思或予以调整,至少针对缺乏条件的资源型城市应建立“收缩态”的转型发展思路,如人口规模缩小、产业特色化等,甚至可以考虑降低行政级别等措施。
新时代,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输出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资源型城市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需要新动能,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建立新思维和确立新路径。我国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方针、路径的设计中,总是尽量规避收缩模式乃至撤销城市建制的思路。这是一种增量思维模式,其实存量、减量以及减量后的重构也是今后一种必然选择。因此,这个新思维的核心是改变传统的扩张性思维,建立“因地制宜”的客观分类思维,按照扩张类、稳定类和收缩类的特征,将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进行大致分类,尤其要将边缘地区、偏僻的山区、生态保护区等综合成本高,后续产业或接续产业无法正常发展的资源型城市归为收缩类的资源型城市,可采取搬迁、收缩等转型措施。相对应,那些区位条件好、资源优势突出、距离消费地或中心城市近、具有一定技术基础的资源型城市才能归类为扩张类或稳定类。否则即使有国家支持,部分资源型城市也可能无法达成绿色、低碳转型的根本目标。
迁移—分离模式探讨
近几年,学术界从资源环境、技术创新、区域发展和社会环境方面,分析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困境,并结合现代智慧技术,从资源环境、区域协调、技术和民生等方面提出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创新路径。然而在我国,无论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三种类型中的哪种类型,都可采用或借鉴一种迁移—分离的建设或转型发展模式,即将资源的生产地、加工地,同市民工作地与生活地通过迁移加以分离,改变传统的将其强行融为一体在衰落期又不得不转型发展的被动现象。也就是说,立足于当代全球化、网络化的现实,将原料生产地仅作为挖掘、开采(可能包含必要的初级加工)的“据点式产地”,而将相关产品的研发、加工和销售基地等布局在区位合理的中心城市中,或者工作地在传统的矿区等生产地,而生活地在中心城市中,人员问题通过通勤方式予以解决。如庆阳市的石油产业,其石油开采生产地分散分布在庆阳、平凉等地,而其石油相关加工业集中分布在庆阳西峰区的产业园区以及西安市等地;工人在矿区上班,但企业总部、生活区和家属主要集中在西安市、庆城和西峰等地。
这种迁移—分离模式不但避免了传统资源型城市的诸多转型难题,而且规避了后面需要面对的就业、社会服务等诸多社会问题,综合效益高,符合社会多元和产业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资源枯竭矿区则完全可通过生态修复后予以关闭,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以玉门市为例,玉门市因地处绿洲边缘的山区丘陵地带,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城市政府坚决放弃了老城区;石油生产工人和设备被有计划地逐步迁移到新疆油田;油田办公、生活基地通过搬迁工程迁址,2001年玉门油田办公、生活基地迁至酒泉,2004年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搬迁至酒泉。现在,市区只设生产作业区,生活区则迁至百公里外的酒泉;在玉门镇建设新市区和实施市政府迁址工程,城市空间功能进行了重构,老市区被逐步废弃,新市区为市政府驻地,还规划了玉门经济开发区、石油化工工业区、建材化工工业区等区域,促进了产业多元化。自2000年开始,玉门市和玉门油田做出迁移决定,9万居民弃城外迁,大片工厂倒闭,厂房住宅闲置,甚至被夷为平地;2009年留守老市区的人口已不超过3万人,仅占原总人口的1/3左右,老城区仅剩无力外迁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和下岗工人等。但外迁后玉门市凭借优越的水土光热资源培育开发的啤酒原料、饲草、肉牛肉羊、棉花、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迅猛发展,促进了城市全面的转型发展,逐步走出了发展困境。
结语
我国资源型城市占国土面积将近一半,其成功转型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但是,基于增长思维和唯城市尺度的产业链创新、拓展和多元化策略未必能达成目标,因为在生态文明建设、成本—效益约束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全球化价值链的层级约束、竞争能力和技术进步限制会约束部分资源型城市的结构升级或替代。在全球化、网络化、生态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应在“双循环”中确立增量、减量相统一的新思维,按照扩张、稳定和收缩三大类分类施策;同时,适应我国部分城市“空间收缩”的国情,一些资源型城市转型可采用迁移—分离的转型发展模式,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作者系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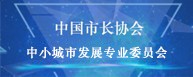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1495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1495